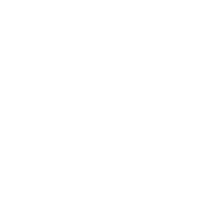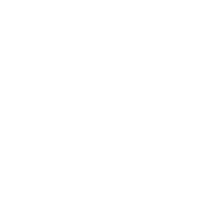自 述
不泯的童年记忆
1926年,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王又得(1900-1971)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母亲栾瑞姺(1901-1973)先是考入协和女子大学,后也并入燕京大学,父母大学毕业后,双双终生从事教育工作。
我的童年是在日寇铁蹄践踏下的动荡年代中度过的。幼年时的许多记忆已然淡忘,唯有两件事,恍然如昨,历历在目。
不满5周岁时,我入小学学习。每日上学路上都要经过一个广场,听大人们说,那是抗日将领冯玉祥将军率领的大刀队操练的地方。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军人们雄浑的吼声,让我每每想起心中便会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冲动。我自幼缺少音律,五音不全,但入学后学的第一支歌,“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胜利,齐欢唱”的旋律却至今不忘,它成为日后很长时间当我遇到难以推辞的表演时的保留节目。
1931年,父亲接任丰滦中学校长一职,我们举家迁至河北唐山。是年,“九·一八”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唐山受累。在唐山市郊大片的农田里,日本兵竖起很多肚子里填满肉的稻草人训练狼狗,破膛吞肉的大狼狗,让我幼小的心灵意识到,稻草人分明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化身。因为经过日本宪兵队门口,不下车鞠躬的中国同胞都会受到稻草人般的同等待遇,被大狼狗咬伤的学生屡有发生。
1954年,冀东伪自治政府的成立,意味着华北的大片区域正在落入日寇的魔掌中。我们沦为亡国奴!当亡国奴的滋味如同大狼狗扑噬稻草人的场景那样,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迹。以致我后来对日本人一直有着挥之不去的复杂心态。这是一段令人耻辱痛苦的记忆,却也潜移默化地在我心中种植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
笃信读书救国
我想解释几句的是,唐山丰滦中学是一所英国的教会学校,父亲从受聘担任该校校长到1942年离任的11年间,几经艰苦经营,修科学馆、建实验室,添置设备,延揽良师,教学水平不断提高,学校得到较大发展。然而几十年来,这些话我一直不敢再提起,只缘当初说了一句学校发展之类的话,招致了我的入党预备期整整被推迟一年的后果。在极左思潮统治的年代,我只能和丰滦中学划清界限。在丰滦中学校庆邀我回去看看的时候,我都没能给其一个满意的答复,想起来也算是一件憾事。
1936年,我考入丰滦中学。浑然不觉中我由一个顽童变成发愤苦读的少年。早年家教甚严,放学后必须先完成当日的功课,再练习一个小时的毛笔字后才能跑出去踢球。及至成年后对体现着中国文化的文字书写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加之周围有些年轻医师字写得犹如“老树杈桠”,横七竖八,纠正起来很难的现实,越发觉得儿童时期的训练让人受益,如若不抓紧从小就接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实在是个失误。
在丰滦中学,我的学习成绩始终保持优秀,这或许缘于背负了父母殷殷的厚望,也与那个时期学校里老师的引导不无关系。教我们化学的是王子承老师,他在河北省各中等学校化学教师的考核中名列第一。物理老师郑昕之,是山东齐鲁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面对老师打开的知识之窗,我尽情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像海绵吸吮水分那样汲取着知识的养分。从那时起,对很多东西都想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好奇心驱使我养成了认定目标锲而不舍做事情的习惯。
教我们国文的是黄肃秋老师,他是燕大的校友,曾参加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担任宣传工作。东北籍的黄老师,才华横溢的文采让我佩服,他的爱国情结也感染着我。在他的影响下,我特别喜欢中国古典文学的诗词歌赋,也崇拜鲁迅、茅盾先生。分析其时的心态,既有积极向上进取的一面,也不乏几许年少气盛的个人英雄主义。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燕京大学、协和医科大学被迫关闭。是年,我报考的三所大学都发来了录取通知。记得在辅仁大学化学系进行口试时,德国神父用英文提问,为什么要学化学?我毫不迟疑应声答道:为了强国!不懂得化学怎么造武器,怎么抵抗敌人?!这可以说比较准确的诠释了我当时的心态——读书救国。我的回答让神父感到很特别,但他仍然在我的报考表上填上“A”。然而,在几经斟酌后,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北京大学医学院。“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1948年我大学毕业。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的六年当中,除了保持中学时期养成的钻研学业、发奋进取的作风外,还度过了社会发生的大变革,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尝到了被奴役的滋味;经历了光复之后国民党的暂时接管;目睹了国民党政治上的腐败。我凭着一腔热血和青年学子的正义感于1 947年投身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潮运动。1949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员。
事物皆需一分为二
1948年,毕业后的我以极大的热情,迎接着北平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到来。翻阅我的履历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我成长的轨迹,从住院医师到科副主任,之后是科主任、院长、研究所长,直至现在的名誉院长。有心人不难发现一个问题,在我的科研成果和学术论著中,2 0世纪5 0年代“开花结果”的屈指可数。我曾经自己统计过,从大学毕业到1 952年2月奉调到友谊医院及以后的十余年间,前后脱产的时间叠加在一起竟达9年之久。当时党员较少,能够写写画画的更少,作为又红又专的苗子我被选拔出来参与接二连三的运动。一场运动约需一年时间,内心不免有些矛盾,看到那些给病人看病的同行忙忙碌碌,真是羡煞不已。
我很珍惜难得的间隙,抓紧一切机会回到业务岗位,努力学习。其实即便在运动当中,我也给自己设置了要完成的“规定动作”。那时,经常是晚上开完会,群众散去后,各小组汇报,我再整理出简报,连夜上送。夜深人静人困马乏,我就采取先睡一会儿,凌晨4时爬起来读书的办法,就这样,看到我整天忙碌的人都奇怪,为什么我的业务没有丢下?天下的事物大抵如此,越是缺少条件与机会,就越觉得应当加倍努力珍惜能够抓到手的东西。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我被撤销了院党委委员的职务,每天接受群众的批斗。直到1969年底1 970年初,我被派到京郊房山霞云岭公社下乡医疗。突然一日通知我速回,派往青海。我搭坐在满载煤炭的卡车上,顶着凛冽的寒风回到医院。此时,我爱人受命带领天坛医院的一支医疗队到甘肃支边,安家落户。鉴于我一双儿女一个在东北兵团、一个在内蒙牧区插队,上级同意了我的请求,不去青海,而以随迁家属的名义跟我爱人一起去了甘肃庆阳。
我从去青海被改派到甘肃庆阳这个贫困偏远的山沟沟安家落户,一呆就是四年,连混着杂草、羊粪的窖水都金贵如油,生活的艰苦自不必说,但是这四年却让我受到深刻的教育。在这里,我真正接触到了最底层的农民,看到了中国农村的生存状态以及缺医少药的程度,这些都是我在城里根本无法想象得到的,由此也引发了我对很多现实问题的思考。
那时,陆续有结核性脑膜炎病人找上门来看病。这引起我们的警觉,必须控制传染源,否则可能造成结核病的流行。凭着职业的责任感和对当地穷苦群众的极大同情,我们推着独轮车,拉上柴油发电机和一台200毫安的×线机,翻山越岭来到发现病人比较集中的大队,在窑洞里架起机器,给村里的群众做普查。在与大队支书商议治疗的事宜时,我大致估算了一下,就是买最便宜2分钱一片的异烟肼治疗这些病人也要200元。支书的一句话让我们凉透了心,“没钱!”温饱尚且解决不了,何况治病?我们忧心如焚却无能为力,本想办一件好事,因为经济条件差,用西医治疗病人的路被彻底堵死了。
在条件艰苦的庆阳,唯一能做的只有就地取材,对症处理。我们和赤脚医生商量后,决定自己动手上山采集中草药,把百部等一些对治疗结核有效的草药采集到一起提供给病人服用。中医中药真的成了“管事儿”的看家宝。在当地,有的妇女找到我看病一言不发,把手往桌子上一放,意思是先摸脉,听我说的对路,她便打开话匣子什么都讲,不对症,她拔腿就走没商量。下放的这四年,我拜当地老中医、赤脚医生为师,走进深山密林,认识了几百味中草药,学会了一些中药简单的炮制方法及三四味中药便能治好老乡病痛的本事,也是在给贫下中农治病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一些经验。后来,我之所以坚定不移地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课题研究,与在庆阳被“逼上梁山”这一段背景有很大关系,因为不懂得中医的大夫是个“瘸腿”的大夫。
走中西医结合之路
1966年4月,彭真同志亲自对我说,你们要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指示。但是宝库里究竟能藏着什么宝?此前,很多人也听到过毛主席1958年这一批示,不了解,并不以为然。
真正让我感悟到中医神奇的是发生在1964年早春时节的一件事。那天,妇产科收治了一位妊娠8个月盆腔化脓感染、伪膜性肠炎的患者。病人高热合并中毒性休克,一天二三十次海水样大便,脱水、休克,危在旦夕。全院组织了内外妇儿各科的集体大会诊,包括我在内,大家束手无策。猛然间想到中医,将信将疑地请来了著名老中医郗霈龄大夫。郗老仔细地给病人号过脉,开出三付药,并且把辨证施治的理论讲给我们这些西医同道。“分利清浊,养阴清化”果然见效。三剂药下去,病人高热退了,海水样便也止住了,毫不夸张地说真是起死回生!此情此景让我对毛主席所说的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有了最深切的理解。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亲口去尝一尝,现在我终于尝到梨子的滋味。谁说中医药只能在慢性病治疗上发挥作用?在急症治疗方面,它所独具的优势令人刮目。这件事当时在医院引起了
极大的震动。之后我在心里拜郗霈龄老中医为师,成为我学习中医的起步。在经历了甘肃庆阳缺医少药“草根”治病的那一段锻炼,我更抱定了学习中医的决心。从甘肃回到医院,我就致力于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把目标锁定在两个课题:逆转肝纤维化和抢救多脏衰。一手抓慢性病治疗,用中医中药阻止逆转肝脏纤维化向肝硬化的发展;一手抓急性感染合并多脏器衰竭的治疗。实际上,这种选择与中央多年以来一直强调要发展中国医药学、中西医取二者之长、融合一体、优势互补的精神相吻合,也成就了我们几十年走过探索之路,我们医院在小儿肺炎、艺术嗓音、逆转肝纤维化、抢救多脏衰等方面做出成绩,形成友谊医院中西医结合的特色。
那时,我们经常下了班几个人凑在一起研读中医经典医著,研究温病传变、卫气营血在临床上的应运之道,有了庆阳的摔打,回过头来再系统地学习中医,自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以感染性多脏器衰竭治疗为例,西医在抗感染、抗休克等方面的长处,包括肾透析在内,都是比较有效的办法,但它也有无计可施的尴尬,比如急性胃肠衰竭,腹胀不排便,而这恰恰是中医的独特之处。中西医结合必须要优势互补。我们研制了促动合剂(后改名为通腑颗粒),在解决西医难解之题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提到我们治疗感染性多脏器衰竭的实例,很自然让我马上联想起马力。那年某大学一年级的同学参加军训,几十个人突发中毒性痢疾,马力最严重,并发多脏器衰竭住进了北京市某医院。晚上市卫生局医政处处长紧急电话叫我去会诊,我到后先是检查病人的基本情况,患者呼吸窘迫,血压不升,弥漫血管内凝血及肠道的茵群失调,仔细一了解,这个医院连基本的抢救设备都不具备,我决定迅速转到友谊医院治疗,市领导、中央领导先后打电话特别要求我,一定要全力以赴,抢救成功。正是在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优势互补指导思想的引领,我们日夜守护、精心治疗,当初奄奄一息用救护车拉进来的马力,半个月后活泼如初走出了医院的大门。
融贯中西
硬化了的肝组织还能再变软吗?过去,国内外医学界一致认为,硬化了的肝组织已经广泛纤维沉积、形成结节,是不可能恢复原性状的。肝硬化的病人就像被判了无期徒刑。对于我为什么选择了许多人都认为可能是颗粒无收的这条攻关之路,有的记者把原因归结为,是我对祖国传统医学的深彻感悟,具有创新精神,其实,我认为最主要的应该是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负责。
多脏器功能不全的发生是一个从轻到重连续的病态发展的过程,如能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必有利于提高抢救的成功率。我们提出的多脏衰分期诊断标准,在1995年被中华医学会急诊学会和中西医结合学会联合召开的全国急症会议采纳并纳入全国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我们又总结出了本病的四个主要中医证型及相应治疗原则和方剂。由于重视了早期识别、早期治疗和中西结合治疗,显著提高了抢救成功率。因为多脏器功能不全的病死率由1985年前50%下降至90年代28.4%,多脏器衰竭为50.94%(国外同期分别为60%和62.5%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们的科研屡屡获奖。
我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国外医学专家常常问我同一个问题:“你的药里是什么成分在起作用?”这个问题必须回答,这是关系到我国传统中医药走向现代化、国际化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像西医新药研制那样,让中医也先找出成百上千种单一化学物质,逐一试验效果的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怎么办?
首先,通过中医的辨证施治选出几组药方,在临床应用观察,取得良好疗效后,再应用分子生物学、细胞学、组织化学手段对药物和病理对象进行深入分析,找到药物作用原理和药物作用的病理靶位,在此基础上对药物重新提炼组方,通过中西结合不断上新的台阶。我们对肝硬化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国际公认的研究模式,从人血蛋白免疫损伤性大白鼠肝纤维模型到细胞水平、分子水平、胶原基因的转录等,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我们还根据现代医学的观点,结合祖国医学辨证理论研制出中药复方制剂,并以细胞、分子生物学乃至基因芯片(初步)等方法从动物整体、细胞、基因表达多方面探讨胶原、胶原酶、基质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物、细胞因子、细胞内信号传导的变化规律,阐明中药的作用机制,是在多层次、多靶位上纠正了纤维合成及降解的失衡。经过动物实验及体外肝星状细胞培养的细胞分子生物研究证明,中药通过抑制炎症,又直接抑制了星状细胞的增殖及纤维化过程的自行延续。逆转治疗的关键在于有效地控制炎症,抑制胶原合成,促进胶原的降解,并力求恢复二者的平衡。对于我们作出的结论,国外西医专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像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前院长、国际肝病学会前会长卢丁·史密特教授就说,王教授,你们用10味中药,严格地以现代医学手段证明可以减轻和部分逆转肝纤维化,是在这一极端困难的实验领域中的一项突出贡献。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舒潘教授提出,我们所用的研究方法是国际认可的,研究水平是高的。
医学是人类共同的科学,在新理论、新成果不断涌现的今天,我始终坚持,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必须加强与国际的交流和沟通。搞中西结合,切忌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要善于兼容并蓄,博采众长。
技到用时方恨少
在甘肃庆阳的时候,我遇到一例最困难的病人。一名病人子宫大出血被送到我们这里时,血红蛋白只有每百毫升一克多一点,按照常规这样的病人需要做子宫摘除手术,但是这么低的血红蛋白能否承受得住手术,大家一时没了主张。看着病人的情景已经不能再拖了,必须马上进行手术。我说做。但怎么做?全麻肯定不行,我们决定实施针灸麻醉。在针灸麻醉下为病人做了子宫摘除术。
这个病人需要紧急输血,没有血库,只能就地解决。紧要关头当初接受住院实习医生培训和住院医师培训时所学习的如何查血型、配血的知识救了急。
此后又遇到数次紧急的情况,不少都是沾了当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光。每当回忆起这些细节,我都禁不住要大声疾呼,住院医师培训工作太重要了!假使那个时候没有我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受到过的相关训练,即便有全心全意救治病人的愿望,也很可能化为泡影,缺少操作技能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病人痛苦,甚至死去。一个医生他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本领,要靠在实践中不断地磨练,但基础牢靠与否,与规范化住院医师培训密不可分。这一点,在远离城市的山沟沟,我的体会是那样的强烈。
目前,我们医院正在推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试点工作,很多人反映这项工作难度很大。我看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与现任科主任这一级的同志没有接受过规范的培训背景有直接的关系。人们常说断档,就表现在这里。最高的奖赏,无声的命令
我从甘肃庆阳回来后,给我们科室订下16个字的科规。抢救马力的过程也充分体现了这16个字的精髓——全心全意、千方百计、争分夺秒、认真过细。全心全意自不必说,每个医务工作者都必须要全心全意对待患者及其家属;千方百计实际上浓缩了技术上必须要精益求精,有“招儿”能解决问题的内涵;后两条则强调确保病人的安全不仅要迅速,而且要严谨。这十六字方针至今仍挂在医院ICU的墙上,鞭策着院内同道在临床医疗中践行。说起来这1 6字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在庆阳抢救贫下中农时大伙总结的心得。在我以为,病人的病情就是无声的命令,这是医生的职责所系,由不得你去考虑个人利益得失。当初我决定把马力转到医院来,有人好心提醒,这样做风险太大,万一病人出现不测,住在原医院,我们就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可是,病人怎么办?治疗跟不上,是要死人的!病人的安危是头等大事,不竭尽全力抢救还算是个医生吗?
我常和年轻的同志谈心得:与死神赛跑,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看着他们恢复健康,那是对医务人员的最高奖赏。这种褒奖是无形的,心中的成就感会激励自己越发看重职业荣誉与责任,当突发情况出现时,就能挺身而出,置病人安危于心间。
医生要学一点辩证法
我常常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对待事物,要做一分为二的分析。多少年来,给学生上课时的开场白我最爱讲的一句话是,如果希望当一名好医生,你的主观认识一定要与客观的实际尽可能地一致。至于怎么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就需要学习辩证法,研读实践论和矛盾论,从中领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直到现在我依然坚持这个观点不曾改变。
在这方面教育我最深的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祝寿河同志。业内同道皆知,祝寿河是著名的儿科学家,是他提出了微循环障碍学说,这和他具有辩证法的思想、勇于创新的精神密不可分。他提出使用阿托品和654-2抢救小儿中毒性痢疾、中毒性流脑、并发多脏器衰竭,若以当时书本记载,阿托品一日极量为1毫克。而他却大胆地用几百毫克把垂死患儿抢救成活。他认为患儿发生极度循环障碍时,机体紊乱的程度,对药物的反应性都已发生了远不同于正常儿的变化。具体事物具体分析,这种极端病态时药物的用量,不能死守常规。祝寿河运用他的新理论,对感染性休克、重症大叶肺炎、出血性肠炎等疾病进行了系统观察,终于创造了用超大剂量阿托品、654-2抢救危重症成活的奇迹。从他的医疗实践中,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事物具体分析。耳濡目染中我受到了许多教益,在实践中也深有同感。例如应用大黄治疗重症感染,正常人服三钱,就会大量腹泻,而在有实热症的患者,为了降温除热,常常要吃一两、二两,不但不会腹泻不止,反而热退神安。我们研究肝纤维化的逆转,就是要看到肝本身内部存在着胶原生成与降解的矛盾,二者失衡就会引起纤维化。抓住这一主要矛盾,用中药复方恢复二者的平衡,纤维化就能逆转。
问到学生有多少看过实践论、矛盾论,结果寥寥无几,这不能不说是个重大的缺欠。临床思维,浸透着对辩证法的理解与运用。譬如一味药,世人都说好,我们做医生的首先要明白是药三分毒的道理,你要有了这种认识,就有意识去弄清它的来龙去脉,这药好在哪儿,最大的功效是什么。同时,它存在的副作用是什么,包括你适用不当产生的不良反应等等,正反两个方面的东西你都弄懂了,你就会得心应手选择最适合的药物。如果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是当不了好大夫的。临床上不能只注意表面的现象,要学会透过表象看到内部的联系,这就需要全面、辩证的看问题,避免表面化和局部的观点,要学会抓主要矛盾。其实,这就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精华。正所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永无止境。就如同毛主席所论述的那样,在真理的长河中,每一段都是相对的真理,而你所能目及的或许现在是对的,但随着不断的探索,可能会产生新的认识,不断修正你以前的看法。
认准靶心矢志不渝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孔子数千年之前便提出了这个问题。及至现在总希望当别人老师的人仍为数不少,这或许是人们普遍的一种心态。然而,当历史将你推至为人师的这个位置上,也不能因为怕受指责而放任自流,必须担当起为人师的责任,还要善为人师。孔子日:三人行,必有吾师焉。对此,我是深信不疑。
科技创新的基础在于人才,谁拥有具有创新意识的科技人才,谁就拥有了占领科技制高点的动力和潜能。我所从事的科研课题主要依靠我和我的课题组构成了一个团队。我从不认为我是什么权威,许多问题的提出靠的是团队,如何做一种动物的模型,如何做一个试验,如何辨证施治,往往是同事们、研究生提出来的。当今,已进入分子生物学时代和信息时代。我们研究问题,只靠书架上几本现成的书是不够的,要运用网络,捕捉新信息、新动态,否则就做不到走在时代前列,也难以情况明、决心大,要讲到运用网络和计算机,我必须向我的研究生学习。只有把老、中、青的各自优势与潜力拧成一股绳,打造一个好的团队,我们的事业才会前进,人才也一定会青出于蓝。截止目前,我所带出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院内研究生已六十余人。他们分布在各地,有不少人已成为学科带头人。
对我的研究生教育工作,贾继东同志总结得比较客观,我强调搞科研课题研究,应该是打靶而不是打鸟,打鸟是看到哪棵树上落着鸟就举枪,东打一枪西打一枪,打下来的东西不成体系。而打靶则是认准了一个目标,数年甚至数十年都朝着这个方面努力,从未动摇。正因为此,我们才做出了一些成绩。打鸟打靶的比喻,其间蕴藏着深刻的哲理。这也不是我的发明,原卫生局长已故的阎毅同志就不止一次如此说过。
月是故乡明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诗人的声音穿过千年的白露与夜晚,道出了我们最不容易辩驳的爱家爱国理由。我自幼经历社会的动荡,打心底里渴望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希望祖国昌盛。月是故乡明寄托着我“思乡”的感情。
1989年春,我的心脏冠状动脉三个主要分枝已堵塞了两枝半,决定去美国做心脏搭桥手术。临行前,独自坐在办公桌前思绪万千,遂在小黑板上写下了五个大字。结果等我5月30日回到办公室看到了依旧还在的“月是故乡明”,真的是感慨良多。这就是为什么在当时美国的电视报纸铺天盖地报道我国发生的情况,很多人劝我不要回来,而我一门心思认定只要民航有班机落地北京,我就一定要回家的真实心态。我前后出国四十余次,记不清多少
次有人诚心挽留我在国外发展,并许以重金,包括可以马上拿到绿卡成为永久性居民,然而,所有这些与我的追求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我关心的是医学专业的进展,感兴趣的是有机会与各国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共同探讨大家关心的专业话题,并把最新的发展动态带到国内,总结制定适合我国的标准和治疗方案,在全国推广应用。
尽管我们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暂时还赶不上一些发达国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憾,但这里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的事业在这里,我的感情在这里,我的根也在这里。月是故乡明。
快乐地工作
时光荏苒,我已步入耄耋之年。81岁了,该怎样给自己的人生划个句号才算圆满?这是时时萦绕在我脑海中的一个问题。
孙女曾劝我说,爷爷,地球离了您就不转了?我说,没有。孙女说,那您是不是觉得开什么会,您不坐在那露面心里就不舒服?我答,也不是。孙女说,那您就该把一切都拿掉,把用在工作上的时间和精力转移到您喜爱的诗词歌赋、观赏山水怡情上来。
讲真心话,我自知已到了风烛残年,犹如一根蜡烛烧得只剩下不多的一小截,但我由衷希望能够在这星星光亮尚存之际,还没有熄灭的时候再多做些事情。假使让我现在扔下这些悬而未决的科研问题,扔下应该做而不去做的工作,我扪心自问,真的很难、很难。孙女的建议恐怕我一时还难以做到,逐步去完成吧。但我会逐步地将任务交给年轻的同志去完成,趁着头脑清楚的时候,多做一些总结性的工作。人生本该如此,活到老就要学到老,就要实践到老。
我会听从大家的劝告,注意保重身体,争取多活几年,找些快乐的事情来做。比如,我现在仍然在学习英文,把那些很难听得懂、原汁原味的对白弄清楚;把一些科研课题的解决途径理清,包括吟咏一些烂熟于心的唐诗宋词,这些于我,都是很快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