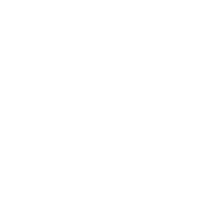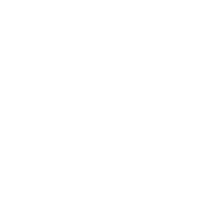我与王老的半世师生情——查良镒
我是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医预科,一年以后又转入北大医学系的。1953年开始上临床课,我们班的同学多,当时的新中国急需大批医生,经过院系调整,我们1950年入学的和1949年入学的合并成一个大班,有212个学生。当时,北医的附属医院安排不了这么多学生上临床课,于是很多人就被分配到北京当时的几个大医院。我虽然是在人民医院学习,但早就听到去同仁医院实习的同学说:同仁内科有位王宝恩大夫很高明,教得特别好,曾从师于著名的临床内科兼生化教授刘世豪,业务基础尤其扎实。带同学讨论病例时善于启发,由浅入深,最后的总结也特别全面,上完王宝恩的课以后,印象特别深刻,是他们当时最为佩服甚至有点崇拜的临床老师。这是我知道王教授的开始。
真正见到王宝恩教授是在1958年。当时中苏关系有所改善,苏联要派一批高级教授到北京友谊医院工作,为了要配备好向苏联教授们学习的骨干,也为了要加强医院的技术力量,由北医附属医院调来王芷沅、黄慧英、李松年和我,由同仁医院调来了王宝恩,由协和医院调来顾复生。
可惜时间不久,我又从内科转入同位素科。虽然我在北医一院时即已被安排加入郑芝田教授为首的内科消化组,但也得服从分配,改为学习放射性同位素,这在当时是一门崭新的学科。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在医院工作的苏联专家全部奉命回国。我们这些人随后接受了要“发奋图强,自力更生”的教育,就是我们要自己干,而且干的要比苏联教授在医院时更好。后来我就开始和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同道们一起,研究用放射性磷32治疗恶性肿瘤胸腹水的新课题。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期间,粮食定量不足,副食严重短缺,又加上放射防护条件很差,在将放射性磷32标记成磷酸铬制成可向胸腹腔注射药物时,我要接受大量放射线照射,我曾经向苏联专家学习过放射病的知识,深知放射线对人体的严重危害,但在希望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理念下,日夜奋斗,努力工作,特别是开始应用的几例病人初见成效,更增加了努力工作的动力。
但科学究竟还是科学,随着连日连夜在几乎没有防护放射的条件下工作,我出现了胃痛、消瘦、原有的溃疡病复发,但我仍继续坚持,直到反复发作肺炎、肝功能出现异常,患上了浮肿病,我爱人又发生了葡萄胎。我和几位挚友们再三反复商量后,决定不能再接受放射线了,就请求调离,改换门庭,投奔内科王宝恩的门下。
由1962年到1992年,除了文化大革命中及王教授下放甘肃的四年多及我去美国的近三年时间以外,我一直接受王教授的培养、教育、指导和帮助,我一直把王宝恩作为老师,作为要努力学习的榜样。
1962年开始,我是消化组王教授的助手,当时三年困难刚过,食品供应突然改善,饱受饥饿之困的不少人都大吃大喝,身体由瘦而胖,其中有些人逐渐出现了肝区胀痛、乏力、疲倦症状、转氨酶升高等。为什么营养好转而肝功能却转坏?这是当时临床面临的一大难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省级领导,他肝区痛、肥胖、肝功能很差,在当地经过多方面治疗无效,是被人用担架抬到病房里来的。经过王教授的直接指导,并经过病理科的证实,他实际上的诊断是重度脂肪肝。经过综合治疗,逐步增加运动,减轻体重,最后肝功能恢复正常,病人愉快地甩掉拐杖,走着出了院。自此以后,大批脂肪肝病人都在明确诊断后接受综合治疗,陆续痊愈出院。王教授及时地总结出一套关于脂肪肝的理论及实践经验,包括临床、化验、病理、超声波检查的特点等等在国内发表论文,在同道们之间交流推广。当时对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脂肪肝,鉴别肝炎和脂肪肝,以及综合治疗的特点等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63年在汤进院长的领导下,开始了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和科研。王教授亲自带头向中医医院的著名老中医郗霈龄老大夫学习,和郗老一起为病人看病,学习开中药方,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诊治不少病人,包括急性感染、败血症、伪膜性肠炎、肝病的治疗等。王教授既带头认真学习,又善于总结,先后用中医的活血化瘀、清热解毒、分利清浊等治则及辩证施治的方法,治疗了大批危重病人,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开创了中医中药、中西医结合治疗急症病人的先例。可惜这些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而被迫停止。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文革后逐渐发展成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种急性感染、败血症、重症肠炎、胰腺炎及多脏器衰竭的抢救治疗等等,救活了大批病人。
这些治疗急性感染,特别是难治性肠炎的治疗经验,我一直沿用了数十年,包括国内、国外,屡用屡见效。
当年消化组的研究工作,多是由临床需要的实际出发的,当时发现郊区的一家工厂不断送来肝病的病人,包括一些重症肝病患者,而且日渐增多。为了查明其原因,由王教授领导组成了肝病治疗组,在厂医务室的配合下,对全厂工人及家属进行了全面普查,为了减轻病人及其家属的来往奔波,还在工厂内组建了病房,分组治疗定期巡护,深受到患者们的欢迎和表扬。此外又和谭柘寺的肝病疗养院协作,每周定期去查房巡诊。这些体现了为病人服务的行动和措施,在文革中被错误批判为“拿病人做试验”、“拿工人做试验”。我却一直不能同意,也不能接受。
王教授在担任临床、教学、科研和行政领导等繁重任务同时,还负责着北京市领导彭真、刘仁等的保健工作,一个电话就要去出诊或是出差。
1972年成立干部病房以来,我们一直遵循的精神就是:全心全意、日以继夜、无偿劳动、心甘情愿、任劳任怨、刻苦钻研、勇于负责、勤于思考、以我为主、借鉴外援、集思广益,力争用临床医学的最高水平,把保健工作和疾病预防工作,做到好上力口好。
由于多年来的突出贡献,王教授在2005年获得卫生部中央保健局所授予的“特殊贡献奖”。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奖,每个人只能获得一次,这是授予那些多年来对于首长保健有突出贡献的医生专家的,王教授很荣幸地成为其中的一员。
王教授还和祝寿河教授等一起,在1965~1966年对654-2进行了研究,这是一种由植物的根部提取出来的药物,在65年4月完成第二次的人工合成适于临床应用的制剂,于是称为654-2,学名为山莨菪碱。它不仅可以缓解痉挛,止恶心、,呕吐、腹泻,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微循环,对于抢救各种感染致成的中毒性休克,往往有起死回生的功效。王教授在内科,祝寿河教授在小儿科,密切的观察,守候着病人,挽救了不少危重病人的性命。其用药的关键是掌握其剂量,必要时不是1毫克、2毫克,而是30、50、甚至100毫克或更多,这剂量的掌握在于密切而细微的临床观察和当机立断的掌握时机,此药还适用于有机磷中毒的抢救,而且一直应用到现在,这些都是当年王教授和祝教授奠定的基础。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殃及友谊医院。王宝恩老师也被打成友谊医院三家村中的一家,特别他又是彭真、刘仁的保健医生,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我作为王宝恩的助手,也成了革命对象,在内科走资派中排第七,曾在内科批斗王宝恩的大会上被揪上台。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运动,我不但跟不上,而且想不通,突然好像过去是对的事情,一切全错了。过去的工作越努力,错误也就越大,在批斗会上,“革命”群众要我低头,我心里是既生气又好笑。
一场政治的急风暴雨过后,我和王宝恩的联系不得不中断。他长期在专政队里受苦、受难,受到监禁隔离、消息不通,我非常同情又爱莫能助。后来客观条件稍有改变,为了让王教授了解更多的外面信息,我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后来的邮寄,用“梁毅”的笔名,暗传消息,报告当时的院内外形势和应该注意的事项。
1969年冬,王教授随其在天坛医院工作的家人,下放甘肃庆阳。临走之前,他把一个沙发椅送来我家寄放。经过红卫兵抄家,我们家里的沙发都被抄走,这沙发就成了我家里唯一的一个。以后我与王教授不断有书信来往,我知道他在甘肃全心全意地为老百姓服务,干得很好。他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用各种办法给人治病而获得好评。我也知道有的当地老百姓甚至认为王教授是刘少奇的保健医生,往往从周围很远的地方,翻山越岭地来看病。在当地多次上了广播、报纸,并拍成了电影,成了医生明星,是大大有名的好医生,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事。
1972年由于连续有几位部长级干部的溘然长逝,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要成立干部病房,设干部门诊。我经过白思温同志的推荐,由二医借调回友谊医院负责干部医疗工作,我经常感到自己的知识、经验不足,缺乏老师的指导,医院里的医疗水平不高,军代表在当家,各方面制度不全,颇有些混乱。我坐在王宝恩寄存的沙发上时常想,如果王教授能够回来的话,工作就好做的多。
1973年王老伯母病逝,王教授回京奔丧,我得以更明确地知道,在庆阳的地广人稀,病人不多。王教授虽然在当地深得好评,但各方面条件很差,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我了解到诸方面得情况之后,决定尽自己的努力,由大局出发,争取把王教授调回来。
我在努力做好干部病房工作的同时,也利用各种机会向当时的各方面领导反映,医院里缺少王宝恩这样的人材,迫切需要王教授的回来工作,首先得到医院里诸多老领导、老同志,特别是白思温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他出了许多主意,做了很多具体的指导。
我多方努力,先后向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的领导、有关单位军管会的负责人,当权的军代表、卫生部的领导等多方面反映情况,最高级的找到了当时的卫生部长、北京市的最高领导等。凡是有机会、有可能的,我都不放过。大多数领导表示了同意,但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未结束,不敢违背“6.26”指示。有的人回答的颇婉转,说“困难很大,以后有机会再说”, “等一下,慢慢来”等等。一次次的努力都未成功。但我从来也不灰心,绝不放弃,前后失败达1 1次之多。
终于第12次机会来了,1973年当时香港新华社梁威林社长住进友谊医院,他先后数次住院,每次的治疗效果都很好,我们不只是简单的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他是我衷心佩服的老领导。他工作很忙,住院期间仍经常因公外出,我就寻找机会和他长谈,禀报了医院的情况之后,他爽快地表示愿意帮忙。我知道他来北京都是向周总理和中央领导禀报工作的,他是叶剑英元帅的老战友,又都是广东人。
梁威林同志建议我们要请钟惠澜教授出面写信,这样更容易得到领导重视,效果会更好;他还提出用毛笔写,用楷书写。我向当时医院老领导,白思温、张彤、黄慧英做了报告。他们按照梁威林同志提出的要点,起草拟稿。我跑到琉璃厂文具店里选购了当时最高级的、最昂贵的狼毫毛笔,请我那高度近视的老父亲,带着厚厚的眼镜,照着底稿,用工工整整的楷书,横平竖直,一笔一划,排列整齐的认真抄写,完成后又请院领导和梁威林同志审阅。最后由我和白思温骑着自行车去钟老的家里,说明来意,征求意见。钟老仔细看过以后,欣然同意,立即签了名,并且表示希望能办得顺利成功。再由院领导看过钟老的签名信后,由我郑重地送给梁威林同志转呈中央最高领导。
后来梁威林同志告诉我,这封信由叶帅批示后,转给了中央政治局,多数政治局委员表示了同意。梁老随后高兴地告诉我:“看来是成功了。”后来果然是一路绿灯,进展出乎意料的快,由中央到省、到县,王教授很快接到了调令。
当时北京市卫生局老局长闫毅同志患鼻咽癌已进入晚期,我就急打长途电话,又发电报,请王教授尽快回京。王教授立即很快赶回,参加了闰毅同志最后的医疗和抢救。
王教授调回医院后,即被任命为内科第一主任,在科领导的岗位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时过不久又刮起了“反右倾翻案风”,医院饭厅里出现了有针对性的长篇大字报,主要内容是说王宝恩的调回违反了毛主席的“6.26”指示,硬把王教授的调回与“右倾翻案”联系在一起。我当时却处之泰然,因为这件事是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决定,这种大字报根本不屑一顾。而不久之后,这股风也就烟消云散。
时间又过了几年,叶剑英老帅病重,负责治疗的医疗组长通过院领导,请我参加叶帅的医疗组。这位组长曾率领解放军医学代表团访美,参观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时,我正在该院并有幸应邀担任翻译和陪同,他们了解我的水平和临床经验。我当时真是感到非常荣幸,感谢他们对我的充分信任和邀请,但我觉得自己的医疗水平和经验都不如王教授,而且这正好是答谢叶帅的难得机会。我考虑了一下,就说:“谢谢您们的信任和邀请,我的水平和经验都不如王宝恩教授,他是我的老师,也去过美国讲学交流,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是否可由王教授来代替我?”他们经研究,表示同意。就这样王教授参加了叶老帅的医疗组,一直到叶帅生命的最后时刻。王教授用他的丰富临床经验,以实际行动回报了叶帅当年对他的帮助和支持。1979年初,我作为访问学者奔赴美国,在巴尔的摩市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附属医院,成为该院在间隔30多年以后,第一位长驻该院的中国大陆医生。当年9月我有幸参加中美建交后派出的第一个访美的中国药学代表团,在美国几个著名的药学院校、药物研究所进行访问和交流。我虽然在团里是做翻译、联络和负责安全工作,但从中我深刻体会到中国和美国在完全隔离几十年以后是多么的相互不了解,又多么的希望相互了解。当代表团顺利地完成访问以后,在旧金山三藩市机场,我送代表团西飞回国,我一个人又向东飞返巴尔的摩市,在万尺高空的飞机上,我就萌生了请王宝恩教授访问美国的想法,我估计王教授如能访美会很成功,一定会受到热情欢迎,对于中美医学交流的双方都会大有好处。
我先和我的导师贝莱斯教授商量,又与该校多位教授和朋友协商,我介绍了王教授的简历、经验和研究工作等诸方面,得到了他们一致的赞成和支持。在得到王教授的同意并确定了他来美的讲演题目和摘要以后,很快的就向北京发出了正式邀请函,并按照我刚学到的美国医学界安排学术报告的办法,开始了紧张忙碌的联络工作。当时还没有传真机,更没有现在的网上通讯,我到附近的二手货商店,买了一架旧打字机,用极不熟练的缓慢手法打字,开始发信联络。来往的书信、函件在书桌上叠起来竟然有一尺多高。1980年中美刚刚建交,美国的医生、教授、研究人员很迫切地愿意了解中国。我的来信几乎无例外的得到极为热情的欢迎,我寄去的王教授的简历、研究领域、发表的论文目录和演讲的题目,他们都有兴趣,随后即要确定双方都适合的时间、地点,确定接待的负责人、机票、航班、住宿安排、交流活动的具体项目,每天的活动日程以及酬金等等。还要照顾到各地活动的连续性,美国的地方大,务求不要跑回头路,要一站连接一站,就这样安排了王教授访美先后共8周的参观访问。从1980年4月至6月一共访问了美国14个城市,24所医院、研究所和医科大学。每到一处都发表学术报告,相互交流,参观访问,每处少则停留两三天,多则四五天,个别
的,如去五大湖旁边的Milewaukee则停留了一周。最高级的住宿是大饭店中的总统套房,最差的时候也曾在我国访问学者的宿舍里睡地铺。王教授的英文好,表达能力极强,他用自己在中国的扎扎实实的医疗工作和科研总结,按照国际上学术交流的通用方法,有数字、有统计、有统计学处理。有分析、有结论,介绍了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对严重感染的治疗,在美国的医学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我这里只简单说一下王教授在美国的第一场讲演,地点在我当时学习和工作的著名学府,约翰.霍普金斯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举行,这所医科大学先后有过十多位获得过诺贝尔医学奖、生理学或生物学的著名教授或医生。
为了这次讲演,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先进行了彩排,请了美籍华人教授来先听一遍,做了修改、润色和补充。当天在医院的大礼堂早已坐满了老老少少的医生、教授和研究人员,还有不少医学生。王教授以中医对于严重感染的治疗为题,介绍了对于败血症、急性胰腺炎、各种严重感染、食道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等的治疗。会场一直静悄悄的,讲了45分钟报告结束,获得了响亮的掌声,随后的15分钟是提问,王教授又一一进行了高水平的回答,几位著名教授先后站起来用惊奇、钦佩、赞赏、没想到等词语对王教授的报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一次又一次的热烈掌声中成功的打响了第一炮。散会后很多学者、教授不肯离去,纷纷前来握手致意或提出问题。随后,医学院的刊物、当地的报纸、各方面传媒纷纷发表新闻或消息,介绍了中国教授的精彩讲演。他们能够听得懂、听得明白能够理解的讲演,讲中医中药的成就,能够这样的受到欢迎,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是第一次。
随后,王教授和我按照预定的计划,遍访了包括哈佛大学、Mayo临床中心、斯坦福大学医院等著名学府和医院,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由东到西,由南到北的学术交流访问。其时间之长,访问的医院、研究所之广,接触到的教授、临床医生、研究员之多,座谈题目之广泛和深入,都创造了中美医学交流的新记录,成为中美医学交流的一桩盛事。在访问的最后又回到了巴尔的摩市。
著名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过研究决定,授予王宝恩教授为医学院内科荣誉教授,这是中美正式建交后被授予的第一位。王教授是带着这样的荣誉,成功地结束了这次美国之行。
在我认识的人当中,王教授的英文水平是最好的一位。他从未去过外国留学,但英文的读、写、听、说无一不精,而且不断进步。他的英语发音本来是带有英国口音,80年到了美国以后,前后不到3个月,他一路讲演,一路交流交谈,英文不断进步,很快的就转为美国发音,并且能巧妙地应用了一些美国谚语,获得了多位美国朋友的好评,特别是那些在美国生活、学习、工作的华人向我询问:“王教授的英文怎么这么好?是不是过去在美国生活过?”
据我所知,王教授的俄文也很好,当年与苏联教授能流畅交谈,他的日文和德文也都很不错。他既有超人的语言天才,又一贯的刻苦学习,努力钻研,而且持之以恒,我当然是望尘莫及。这也是王教授出色地完成这次美国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我知道王教授回国后应邀多次做访美的报告,介绍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带回了不少的新信息。王教授的访美大大有助于不少医学界人士更多地了解美国,特别是为年轻医生和研究生们赴美进行深造和学习,开创了道路。
王教授由1983年至1988年底担任北京友谊医院院长。由一科之主,到一院之长,责任更重了,工作也更忙了。他做院长要统筹全局,同时要医疗、教学、科研、行政都不误。当时的友谊医院是北京市医院当中的重点,各方面的工作都相当不错,在医疗、科研、基础诸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王教授在医院院长的岗位上,充分发挥了他的行政才能、指挥才能。“友谊第一”成为当年流行一时的双关语。
在这段时间里,王教授碰到最难办事情之一是发生在医院的基建过程中。当时在妇产科大楼南侧基建工地已掘成一个巨大长方形的深坑,准备建楼,但遇到卫生局调拨资金收紧的影响不得不“工程暂停”。当时正值夏季到来,如果这深坑里积上雨水,则妇科大楼有倾斜甚至倒塌的危险。王教授多方面反映情况,仍不能解决,很着急,就找到了我,我也觉到形势很紧张,就找到了当时由我负责保健的姚依林副总理,禀报了基建停工带来的危险,得到了首长的支持和帮助。后来,王院长给当时全体政治局委员,每人一信,由副总理的秘书一一上呈。这一次又获得了多数领导的批示支持,使这次基建停工危机,得以圆满的解决。
尽管事后有种种议论,包括有人说:“这点小事,何必惊动那么高层的领导?”但不管如何,反正这一场基建危机得以解决了,不必管他人如何评说。
王教授很重视培养后来人,通过定期的查病房,结合具体病例,分析、讨论、总结,使年轻医生获得提高。他培养出来的学生、硕士生、博士生,质量之精,数量之多,在中国医学界中是不多见的。他的众多弟子在国内、国外已经或者正在取得不少的成就。
我自己有幸由60年代初期到现在,一直深受王教授的培养和教导,由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住院医生,成为后来的消化系疾病专科医生,同时也成为负责保健工作的全科医生。最近十多年又经受了离开北京在海外孤军奋战的严峻考验,我深切地感受到这是王教授多年来亲身培养、言传身教的结果。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在消化病专科的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的情景,那是在遥远的20世纪70年代,刚刚开始恢复学术交流活动的日子。由论文的准备,如何把重点讲清楚、报告的技巧,时间的分配和掌握,一次次的彩排、纠正、鼓励,是王教授手把手扶持着我,使我艰难地走入了学术交流殿堂的第一步。
后来我成为医学杂志、报刊的审稿人、学会的负责人,包括职务的升迁……都少不了王教授的支持和帮助。使我有机会接触专业的广阔领域,同时也锻炼和培养着我的分析、鉴别和评论的能力。王院长还给了我学习消化内窥镜的机会,正是这些使我有可能在随后的医疗实践中,掌握使用这类先进的诊疗技术,确定诊断,安排治疗,挽救了多位病人的性命。尽管现在我自己也年过古稀,仍能不断感受到由于诊疗正确所带来的种种愉快感和成就感。
1978年小平同志提出开放政策,开始向国外选派留学人员,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第一次开始选拔留学人员,要首先参加外语考试。王教授推荐并希望我能够抓住机遇,去参加考试。当时我犹疑不决,实际上是并不想参加。因为第一,我当时身体不好,当年反复发作肺炎加上肝功能异常;第二,我母亲患冠心病,身体很不好;第三,文革期间一切都荒废了,特别是英文,我虽然幼年时学过,曾有一定基础,但那是十多岁的事了。多年来未再接触英文,担心考试通不过。
我还清楚地记得王教授当年最后一次找我正式谈话的情景,当时是在海淀一家俱乐部的前厅,看电影之前,他再一次问我是否愿意去报考英文,并且语重心长地说:“你今年45岁了,以后的机会可能很少了。”我清楚记得那场电影是“红楼二尤”。王教授的一席话,使我虽然坐在电影院里却未看电影,心里展开了激烈的矛盾和思想斗争,当晚我整夜未眠。正是王教授的话和家人的鼓励支持,才使我下了决心去试一试,而这一试的成功结果,导致了后来79年3月的美国之行,也改变了我以后的人生轨迹。
1980年初,我从美国回来后,我尽量参加王教授每周的定期查房病例讨论,凡有疑难病人的重要会诊,只要王教授出席,我就尽量争取参加,充实自己的临床实践和临床思维。
1983年我写的第一本专业书《内窥镜在消化系统疾病中的应用》出版,王教授在百忙之中亲自审阅,并写了序言:“我相信这本书对一般医师和内窥镜专业医师都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对实际工作会有所裨益。”
当时这本书的出版发行时间正好赶上内窥镜由大城市向全国普及推广之际,这本印数8000册的书很快地销售一空。我以后收到多封来信询问何处可买到此书,有人还提出希望再版。正如王教授在“序”中所预言和相信的那样。1986年我的第二本书《胃肠和肝病的现代治疗》出版,王教授当时担任着医院院长,在百忙中他对这本75万字的书又亲自审阅把关。
1992年到现在,我在香港继续为病人服务,每当我遇到难以处理的病人,我就电话向王教授请教,他每次都耐心地解答我的问题,提出的建议既具体又切合实际,王教授一直是我的老师。1986年1月他所创制的中药制剂丹芪和肝冲剂,效果很好,我用其治疗多例香港的肝病病人,多例病人都身受其惠。
王教授80岁大寿即将到来之际,我怀着深切的感激之情,愉快地把我所感受的、亲身经历的一部分写出来。
像王教授这样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根基深厚、学贯中西、既专又全、经验丰富、善于总结、善于分析、灵活敏锐、聪明过人、行政工作能力和组织本领强,在医疗、教学、行政、科研、高干保健诸方面都做出突出成绩的医生,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的教授、硕果丰富的研究家,在中国医务界现存的专家中已是凤毛麟角。这当然有他的超人天资,但更重要的是与他刻苦的学习、超常的工作分不开的。他是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钻研到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我为自己能有这样的老师而感到非常幸福,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我衷心祝愿王教授健康长寿,更希望王教授能注意身体,医运长久。
2006年1月于香港